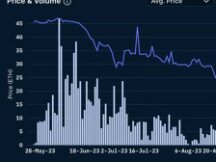“NFT第一案” 二审究竟改变了什么?
业内称为“NFT第一案”的“胖虎打疫苗”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二审判决于年初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相较于一审判决,二审判决虽然未有实质性变化,但判决对NFT数字藏品的定性及业内的相关疑问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与回应。
鉴于我国尚无专门的法律法规对NFT数字藏品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已是从业者识别国家监管风向的重要窗口。为识别判决释放的观点与信号,我们结合本案二审阶段的审理过程撰写本文用以评析其中的争议焦点及结论。
如有不当之处,欢迎留言讨论。
案情概述
被告系某UGC平台的经营主体,其用户A在被告平台上传了侵权作品“胖虎打疫苗”并铸造为NFT数字藏品公开展示及售卖。原告系“胖虎打疫苗”的著作权人,为令被告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中获利,原告代理人购买了前述侵权作品,并起诉原告,要求其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10万元。最终,法院判令被告将涉案NFT打入地址黑洞,并赔偿损失4000元。
争议所在
1、被告平台是否拥有审查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平台在铸造交易环节收取了一定费用,故对NFT数字藏品负有较高的审查义务,通知-删除的审查义务不适用于被告平台。
我们认为,被告未因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不符合承担较高注意义务的情形。
我们需要区分作品上传与作品流转两个行为的性质:在被告平台上,如NFT数字藏品的底层作品存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该侵权自用户将作品上传至被告平台、铸造NFT数字藏品后就已发生。NFT数字藏品在铸造完成的发售与流转均不会对底层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造成额外的侵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结合本案被告为直接侵权人免费铸造了侵权NFT的事实,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被告未从涉案侵权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中获得经济利益,不属于“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情形。
有观点认为:被告免费铸造行为实质上收取了“推广”的利益,仍可适用上述条款认定被告在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问题上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但关键问题在于:增加平台流量是否属于法条描述的“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对此,我们持反对意见:一方面,从文义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应当被理解为盈利,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有形财产,该法条中列举的“一般性广告费、服务费”更是直接将有形财产指向了法定货币,将“推广”利益解释进“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另一方面,从体系与目的解释的角度来说,信息网络传播的过程本就意味着作品曝光度的增加,如曝光与推广属于“直接获得经济利益”,那么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一切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侵权问题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这将导致本条款的界定失去价值,这样的理解显然不符合立法目的。
至于原告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提及的“特定联系的经济利益”,我们认为,被告基于涉案NFT数字藏品流转时收取的费用不属于“特定联系的经济利益”这一范畴,理由如下:
第一,被告基于涉案NFT数字藏品流转收取的费用属于因提供区块链登记而收取的服务费,不属于“特定联系的经济利益”之范畴。具体来说,NFT数字藏品的流转信息需要被记录在区块链上,NFT数字藏品流转时,被告平台必须使用铸造NFT时的联盟链记录相应流转信息并完成流转。需要指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NFT市场OpenSea也以GasFee的名义来收取其提供区块链记录服务的费用,GasFee可达到交易金额的10%。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但书条款内容:“网络服务提供者因提供网络服务而收取一般性广告费、服务费等,不属于本款规定的情形”,我们认为,被告在NFT数字藏品的流转环节收取费用并不当然提高著作权审查的注意义务。
第二,“特定联系的经济利益”应当指的是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可以确定的、与作品相关的、能够由网络服务提供者获得的经济利益。涉案NFT数字藏品仅流转一次,且该流转基于原告代理人的购买行为而发生。换言之,涉案NFT数字藏品具有不流转、被告不获取任何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当被告是否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完全取决于审查时尚不能确定的一种可能性事件时,完全可能存在被侵权人促使该事项发生从而向平台主张责任的情况,这无疑会滋生极大的道德风险——就像本案所发生的。
考虑到司法解释制定者没有在法条中写明“具有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可能性的”或“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的情形以及前述道德风险,我们认为,只有在审查时已经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从中获益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直接获得经济利益”。而本案中侵权作品的交易行为实际上就是前述的在审查时尚不能确定是否可以获得收益的情况,完全存在之后便无人进行交易的可能。事实上,若非原告代理人购买该作品的NFT数字作品,根据购买前该作品的关注度,该作品大概率无法进入流转。因此,我们认为本案的情况不应适用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平台实际上只需要承担一般的注意义务即可。
2、被告平台是否履行了审查义务
一审法院以涉案作品的水印与文字描述作为被告未尽基本注意义务的理由。对此我们持否定意见:
首先,涉案作品存在水印不代表被告未尽基本的注意义务。诚然,水印因指向明确本身具有防伪作用,但涉案作品存在特殊性:作品图片以白色作为底色,且有色的作品内容集中在图片正中央,四周留白较多,色泽与水印极其相近,这就很可能导致审核人员在审查作品时没有注意到右下角的白色水印。涉案作品白色水印与背景的重合已达到一般人难以看清与辨析的程度,不能据此推断出被告未尽基本的注意义务。
其次,被告没有审查作品描述和作者名称具有正当理由,并不影响其已履行注意义务的事实。著作权侵权的是作品,被告审核人员重点审查的是图片本身,而非作者与作品描述。究其原因:作为UGC(用户创造内容)的NFT数字藏品平台,在被告平台上传的作品的很多用户就是普罗大众,随手拍摄的照片、用电脑绘画工具制作的涂鸦等图片都可以是上传铸造NFT数字藏品的底层作品。也正因如此,被告平台的大部分用户有给自己起名的需求,也有给自己的作品起名的需求,被告的审核人员屡见不鲜的是千奇百怪的作品名称与作者名称。
回到本案,涉案作品“胖虎打疫苗”以及作者“不二马大叔”的知名度本就极为有限,在国内知名搜索引擎上搜索作品名称仅会出现本案一审判决及相关宣传文案引发的讨论,何况“胖虎”系藤子不二雄所著世界知名漫画《哆啦A梦》的主要配角,这等起名方式进一步加强了被告平台在审查时的疑虑。
3、如何停止侵权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侵权作品与NFT代码断开链接不足以停止侵权,还需要将NFT代码打入黑洞地址。
我们认为,将涉案侵权作品与NFT代码断开链接即为停止侵权,无需将NFT代码打入黑洞地址。NFT代码只是一串代码,而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是底层图片。被告采取“断开链接”,即,在服务器删除侵权的底层图片之后,用户既无法在选定时间、地点看到侵权的底层图片,用户也无法通过被告平台的APP界面处分NFT代码。至此,被告平台已停止侵犯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
另外,为区别于虚拟货币,国内各数字藏品平台使用的都是联盟链而非公链。联盟链的节点数目有限,达成共识较为容易,打入联盟链的黑洞地址仍是寄希望于平台不作恶,不应作为行业普适的停止侵权方式。
如若被告平台希望侵权作恶,又何须将侵权作品绑定NFT代码,只要在平台上重新展示涉案作品即可完成侵权。因此,对于停止侵权来说,将没有底层作品的NFT代码打入黑洞地址是显然画蛇添足的。诚然,将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无关的NFT代码打入所谓黑洞地址很容易,但我们需要提出明确的停止侵权的方式与限度,与成本无关,与繁琐无关,目的是为NFT数字藏品行业明确停止侵权的路径,法律的适用不需要形象工程。
4、用户购买NFT数字藏品所获得的是什么权利?
一审判决认为:“NFT交易实质上是‘数字商品’所有权转移”,“NFT数字作品持有人对其所享有的权利包括排他性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等”。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为用户购买NFT数字藏品后可以获得完整的所有权。我们对此定性持否定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现行民法典未对区块链的数字资产作出明确定义,根据民法的物权法定原则,司法实践中不得认定NFT数字藏品系所有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虽然部分学者秉持数据、虚拟财产属于物权客体、可作为所有权保护的观点,但学界以债权客体说、知识产权客体说、其他学说(债权说、财产否定说)等学说解释该条款的学者亦不在少数。可见,对网络虚拟财产用所有权来保护至多为一家之言,并非结论,更非真理。何况网络虚拟财产与区块链的数字资产在监管力度上存在明显区分,民法典出台时国内外均未兴起NFT的潮流,相应的学界解释亦不可全盘接受。
第二,允许用户拥有NFT数字藏品的所有权与我国金融监管方向相悖,可能引发炒作风险。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关于防范NFT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指出:不得开展代币发行融资,亦应抵制NFT投机炒作行为。为落实此要求,国内NFT数字藏品平台的特点之一便是记录在联盟链而非公链,且不向用户交付“私钥”,用户不能将NFT数字藏品提取到自己完全控制的区块链钱包,也不能对NFT数字藏品任意处分、收益。这一实践情形恰与一审判决的论述冲突。倘若一审判决的观点被接受,可能会引发用户要求平台完全交付NFT数字藏品私钥、否定交易冷静期等做法的出现,增加炒作与金融化的可能。
因监管原因,用户对NFT数字藏品拥有的“所有权”必然存在限制。那么既然这个权利充满限制,不得排他性占有,也不得任意使用、处分、收益,我们又为何要称其为所有权?
5、NFT数字藏品的交易受发行权调整还是受
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
我们摘选一审判决关于这一问题的存疑论述如下:
A:“不特定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NFT数字作品,属于典型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B:“这种以信息网络途径传播作品属于信息流动,并不导致作品有形载体所有权或占有权的转移,自然不受发行权的控制,亦就缺乏了适用‘权利用尽’的前提和基础”;
C:“NFT数字作品可以无成本、无数量限制复制,即便是合法取得NFT数字作品复制件的主体,其潜在的可供后续传播的文件数量也是难以控制的”。
我们认为NFT数字藏品的铸造受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后续交易则属于权利束或凭证的买卖,与著作权无关。
我们将从NFT数字藏品的整体性质对前述三项问题进行解释:
第一,完整的NFT数字藏品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NFT代码,二是底层的作品,具体到本案,底层作品是图片。我们认可本案的底层作品图片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但“不特定公众”无法获得NFT代码,NFT数字藏品作为整体不符合“不特定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NFT数字作品”的特征。判决只能说:在发行方上传作品后,不特定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NFT数字藏品的底层图片。同时需要指出,NFT数字藏品的底层作品除了图片外还有其他形式,如:音乐。在用户付款购买音乐类NFT数字藏品前,底层作品为音乐的NFT数字藏品并不为一般公众所能获得,这就与一审判决所称的结论更为矛盾。
第二,我们在本案提出权利用尽原则的原因在于:NFT数字藏品(代码+底层作品)的转移,NFT代码正是底层作品的“载体”,出让方会失去对该NFT数字藏品的控制能力,无法像一审判决所说的留下NFT数字藏品的复制品,纵使再购买一份底层作品相同的NFT数字藏品,二者的“载体”NFT代码也是不一致的。NFT数字藏品的交易过程更像是受发行权控制的书籍,只是恰好图片类NFT数字藏品的著作权人同意将书籍内容公开在平台上。事实上,受发行权调整的行为是否要求载体的有形本就是学界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没有有形载体而否定其更适合适用权利用尽原则的事实。国内的数藏行业普遍以“发行”这一词汇作为NFT数字藏品的上传概念,更是在明知发行NFT数字藏品无法撤回的情况下约定了著作权的合作期限,倘若认定NFT数字藏品都应收到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这可能会导致大量著作权侵权的民、刑案件出现,甚至产生群体性事件。
第三,NFT数字藏品的发行数量是确定的,以涉案作品为例,发行数量仅为1份,不具有一审判决认定的“无成本、无数量限制复制”、“潜在的可供后续传播的文件数量也是难以控制”的可能。也因此,一审法院过度扩大了涉案侵权作品可能带来的危害,以至于对一个浏览量个位数的非知名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责令尽到注意义务的帮助侵权行为人承担高达4000元的赔偿责任。
二审变化
对于前述争议,二审法院对涉及一审判决实质内容的部分均予以了维持,但对定性、事实等问题做出了纠正,我们摘选主要的变化如下:
变化一:
对于原审判决采用了“NFT交易实质上是数字商品所有权转移”、“NFT数字作品交易产生的法律效果亦表现为所有权转移”等类似表述,我们认为违反了民法典规定的“物权法定”原则,在NFT数字作品上无法设定所有权。
对此,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中类似上述“所有权”的表述确实存在语义模糊之处,对此应予以明晰。鉴于原审判决认定NFT数字作品的转让行为不受发行权规制,故原审判决中所指的NFT数字作品的“所有权”不应理解为民法中的物权意义上的所有权,其系从数字作品交易所呈现的形式而言,即从形式上看,NFT数字作品交易呈现的后果是该数字作品的“持有者”发生了变更,相应地,基于该NFT数字作品的财产性权益在不同的民事主体之间发生了移转。
变化二:
我们认为,原审法院在指出NFT数字作品交易不适用权利用尽原则时,关于“如果NFT数字作品可以无成本、无数量限制复制,即便是合法取得NFT数字作品复制件的主体,其潜在的可供后续传播的文件数量也是难以控制的”的论述错误。
对此,二审法院认为,不同于传统数字化作品的销售,权利人无法在事实上控制已经售出的数字化作品在后续流转中被轻易复制,NFT数字作品使用的技术可以较为有效地避免其后续流转中被反复复制的风险。
变化三:
二审法院认为,如被告所述,由于区块链上存储空间的限制,多数NFT数字作品的底层文件都是存储在中心化服务器上。本案中,生成《胖虎打疫苗》NFT数字作品的过程中并未在区块链上存储涉案图片,如区块链下存储的底层文件消失,则与之对应的NFT也将不再可用。
但遗憾的是,二审法院认为,在被告平台删除涉案图片、屏蔽该NFT在区块链上的链接地址后,记录了侵权信息的NFT仍存在于区块链上,并未起到销毁侵权信息的效果。所以判决维持了打入黑洞地址的停止侵权方式。
二审价值
虽然二审判决未能妥善解答我们在前提出的全部争议,但作为业内首案及截至目前的唯一中级法院作出的判决,该判决对NFT数字藏品行业形成了若干具有价值的结论,我们总结如下:
第一,明确了用户购买NFT数字藏品后的权利。NFT数字藏品的“所有权”不应理解为民法中的物权意义上的所有权,其系从数字作品交易所呈现的形式而言,即从形式上看,NFT数字作品交易呈现的后果是该数字作品的“持有者”发生了变更,相应地,基于该NFT数字作品的财产性权益在不同的民事主体之间发生了移转。
第二,明确NFT数字藏品与著作权的关系。即,NFT数字藏品的上传与铸造受信息网络传播权调整,NFT数字藏品的交易与著作权无关(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明确了NFT数字藏品停止侵权的形式。NFT数字藏品侵犯著作权的,平台应当断开作品与NFT的链接,并将侵权NFT打入黑洞地址。
第四,明确了NFT平台的版权审查流程。二审判决沿用了一审判决的“一般可能性”判断标准。即应当要求NFT数字作品的铸造者在上传作品的同时提供初步的权属证明,例如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证明其为著作权人或享有相应权利。
写在最后
严格平台责任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与监管实践已成为一种正确,哪怕严格的只有形式,哪怕严格的实质会让平台无法继续经营。
最后与读者分享一则趣事,关于版权审查流程,法院责令平台审查著作权登记证书,对于UGC平台而言,大批量的NFT数字藏品铸造需求意味着高额的登记费用。为确认登记的价值,我们向某地版权局所属的版权登记中心致电咨询其审查标准,得到的回复是:“我们不做实质审查,只要付费,就能拿到登记证书。”

微信掃描關注公眾號,及時掌握新動向
2.本文版權歸屬原作所有,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比特範的觀點或立場
2.本文版權歸屬原作所有,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比特範的觀點或立場